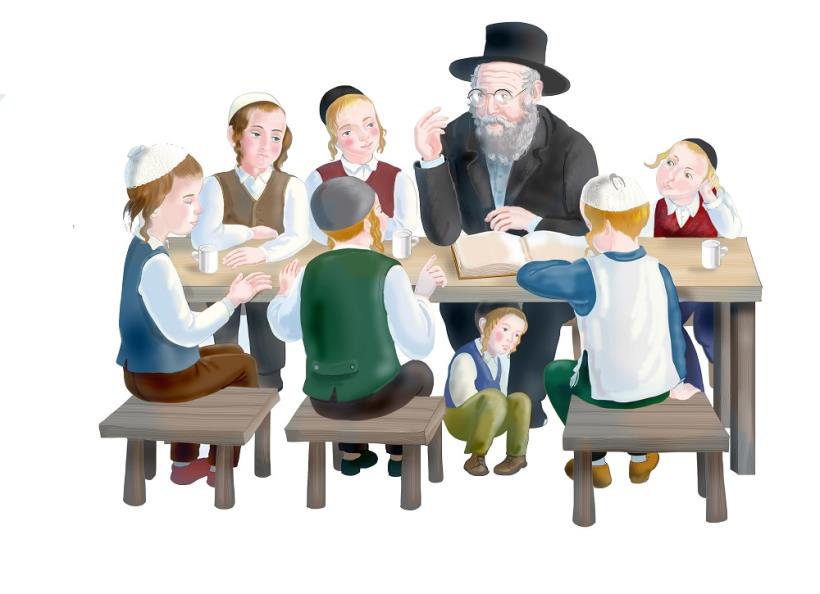
(圖/shutterstock)
我的前一本作品
《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出版後,
陸續獲得許多讀者的迴響。
很多學生或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說,
自己就是那個受傷的孩子。
特別是在讀了第一部分
「受傷的孩子與渴求愛的靈魂」這個章節時,
更是從許多案例故事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孟伶為此前來聆聽我的課程,
並與我在課堂上有一些互動。
她告訴我,當她閱讀了書中的內容時,
才驚覺自己從小到大總是在照顧父母及家人的需求,
而無法活出自己的人生。
繼續看下去...
(贊助商連結...)
聽話的孩子
孟伶目前三十五歲,做了好幾年的保母,
大學畢業後,就待在家裡幫人帶孩子。
除了帶別人的孩子外,也幫哥哥姊姊們照顧孩子,
讓兄姊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去工作。
被幾個孩子綁住常令孟伶喘不過氣來,
父母總會說:
「哪有工作不辛苦,何況,
妳又沒有哥哥和姊姊會賺錢!」
孟伶聽了心裡不是滋味,但也無法反駁。
她常告訴自己,能為家人付出是件幸福的事情,
但心裡總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到了適婚年齡,父母曾急著幫孟伶找對象,
但孟伶被保母工作給綁著,
也沒多餘的時間去約會—或許,
心裡也放心不下兄姊的孩子沒人帶吧!
就這樣一年拖過一年。
直到最近,兄姊的孩子逐漸長大,
孟伶比較有時間可以往外走。
她去參加一些課程,試圖擴大自己的視野。
當社交範圍開展後,認識了更多人,
也遇到了令她心動的對象。
她描述,對方是個外型及個性皆忠厚的男生,
年紀大孟伶十歲,曾經有一段婚姻,
與前妻離婚後,獨自帶著一個五歲大的男孩生活。
孟伶被對方的成熟穩重吸引,
不久之後,兩人展開交往,
甚至有了更長遠的結婚計畫。
幾個月後,孟伶開口向父母提起這位男生,
並說到兩人有結婚的打算時,
父母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寧可妳一輩子嫁不出去,
也不讓妳嫁給離過婚的男人!」
「妳也不想一想,這樣傳出去多難聽?」
「對方還帶了一個孩子耶!
妳不就成了後母了嗎?妳不可能幸福的!」
「我們當然希望妳幸福,
我們是為妳好,難不成會害妳嗎?」
為了證明對方是個值得託付終身的對象,
孟伶特地安排了父母與對方見面。
但不見面還好,一頓飯局下來,
這位男生被孟伶的父母百般挑剔,事
後挫敗地對孟伶說:
「沒辦法獲得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會幸福的,
我看,我們還是就算了吧!」
「難道就要這麼放棄了嗎?」
難過之餘,孟伶想到,
從小到大,自己有好多願望,
都因為父母的反對而放棄了,
而這一次,實在不想再如此「聽話」了!
「我決定了!我不要再當個聽話的孩子了!
這是我喜歡的男生,我的幸福要自己去爭取。
而且,我也不要繼續在家裡當保母、帶小孩了,
我想要去學外語,我想要讓人生有些其他的可能性。」
她告訴我:
「我發現,原來當乖孩子的代價,便是自我犧牲!」
當乖孩子的代價,
便是自我犧牲
孟伶國中時,父親因車禍重傷而不良於行,
長期在家休養,
孟伶便承擔起照顧父親的重任。
哥哥姊姊到外地讀書,
孟伶國中畢業則在家人建議下,
就讀家裡附近的高職夜校,
白天可以在家照料父親的起居,
等母親工作回來後,才出門去上學。
家人常說:
「反正妳的功課也不好,就混個學歷就好了。」
高職畢業後,孟伶繼續念四技的夜間部,
和高職一樣,都是在家裡附近,
念的也都是幼保科。
畢業後,理所當然地在家裡做起保母的工作,
幫社區居民帶小孩,貼補家用。
孟伶的哥哥姊姊都到外地念大學,
畢業後便在外地工作,
接著,進入婚姻有了孩子。
因為忙於工作,
便把孩子丟回家裡給孟伶帶。
他們說:
「反正帶孩子是妳的專長,也不差這一兩個!」
孟伶只能默默接受。
然而,保母的工作究竟不是孟的興趣,
但家人總會說:「妳不幫忙帶,
那妳哥和妳姊的孩子要怎麼辦?」
就讀四技的時候,孟伶在學校裡工讀,存了一點錢,
打算去參加坊間的外語課程,
幫自己的職涯拓展可能性。
當時,哥哥因為創業遇到困難,
需要現金周轉,
母親便要求孟伶把她的存款拿出來資助哥哥,
她也是聽話地把錢交給哥哥。
家人告訴孟伶:
「反正妳畢業後就是在家當保母,
何必學什麼外語呢?」
這句話聽在孟伶耳裡有些刺耳,
但孟伶想到自己有能力幫助到家人,
便自我安慰自己其實挺重要的。
孟伶說:
「其實,一直以來,
幼保根本不是我的興趣。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的是外文。
但是,家人總是說我頭腦不好,
讀外文肯定念不下去。甚至,
當我課業表現得不錯時,內心總有份衝突,
我想著自己應該有能力轉換跑道,
但又想起父親沒人照顧,
家裡的經濟困難,罪惡感油然而生。」
孟伶是個典型的為了照顧父母及家人需求,
過度承擔起家人的責任,
因而需要自我犧牲
或放棄自己願望的孩子。
家人常說孟伶的功課不好,
暗示著孟伶也別奢望有什麼夢想,
孟伶也就如此接受了:
「當大家都說我書讀不好,好像,
我就真的不能把書給讀好了!」
或許,她也不允許自己把書讀好,
她得用這種方式來說服自己,
乖乖地留在家裡照顧家人。
長久下來,孟伶的自我價值
都建立在能為家人付出與奉獻上,
但卻累積了好多的委屈與不甘。
家庭穩定的背後,
常有犧牲者持續犧牲
而這個家,卻因為有了孟伶這個
聽話又自我犧牲的角色,
取得了某種平衡及穩定。
為了讓這樣的平衡穩定持續,
所有的家庭成員會有意無意地
要求孟伶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
而讓孟伶更無法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自幼,孟伶的前額彷彿被貼上一張符咒,
限制了她的行動自由度;
她也逐漸內化了家人的期待與要求,
認為照顧家人需要就是自己該負的責任,
不允許自己有其他的聲音。
事實上,任何系統都要不斷經歷變動的,
家庭系統也是如此。
而系統裡的每個成員,
都需要去適應變動而做出相對應的調整,
以讓系統回到穩定狀態,接著再去因應下一個變動。
當一個家庭系統遭遇危機時,
為了因應危機,總會有個家庭成員跳出來,
暫時承擔起讓家庭系統回到穩定的責任。
為了解救家人,
這個人通常得暫時地自我犧牲。
漸漸地,為了讓系統的穩定狀態持續,
其他成員常會要求這個承擔家庭壓力的解救者,
繼續自我犧牲,甚至認為這就是常態。
如此一來,其他人都可以不用改變,
而整個家庭也都會繼續維持在穩定狀態之中,
每個人都可以活得很舒服。
因此,幾年過去,即便時空環境已經不同,
孟伶的家庭仍然習慣安處在過去的穩定之中,
每個人都依然把孟伶視為
家中那個需要照顧大夥兒需求的人,
並視為理所當然,
甚至連孟伶都如此自我認定而不自知。
持續衝撞,把自己從
自我犧牲的角色中解救出來
而現在,孟伶不想繼續當那個凡事聽話的孩子了。
她需要爭取獨立自主的空間,
她說:「這個家是大家的,
憑什麼只有我在犧牲;
大家都能為了自己的理想去努力,
而我卻只能待在家裡支持大家完成夢想!」
「只是,每當這麼想時,
我便有一份罪惡感存在,
好像在咒罵著我:
『妳不應該就這樣拋下家人的需要!』」
當孟伶能夠看懂,
長久以來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方式,
以及意識到自己持續扮演著過度承擔的角色時,
我是為她感到欣喜的。
然而,另一方面,她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這條路會荊棘滿布、崎嶇坎坷。
因為,她得面對自己的夢想與決定,
難以獲得家人支持的困境,
畢竟,家人仍然活在過去的穩定中,
不想接受任何改變。
同時,還要面對內心裡想要獨立自主,
但又愧對家人的矛盾衝突。
「我現在懂得做出一些反抗!」孟伶說:
「我正在練習,在生活中的小決定裡,
為自己爭取一些主導權,不再那麼聽話了!」
我好奇地問:「那麼,妳的家人有什麼反應呢?」
「超級難以接受的呀!」
孟伶表情誇張地說:
什麼難聽的話,都說得出來,就
是要讓我感覺到愧疚就是了!」
「那妳怎麼辦呢?」
「繼續衝撞囉!」她笑著說:
「我知道我無法改變他們,
但我想透過自己的改變,讓他們知道,
我只是暫時承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
但我不能永遠回頭顧慮著他們。
我有我的人生要過,
而他們的人生,
也得由他們自己去照顧。」
她用輕鬆的口吻說著,
但我知道這過程一點也不容易。
雖然,孟伶仍然在家做著保母的工作,
但現在,她會撥出更多時間去參加外語課程,
花更多時間閱讀,
以及,參加心理成長的課程。
同時,她與男友持續為了
步入婚姻而做著各種規畫與打算。
她知道,無論在生涯或感情上,
要得到父母或家人的支持也許很難,
但如果現在什麼都不去做,改變是不會發生的。
看更多好書試讀:
- 世界最窮總統穆希卡演說時,台下的媒體幾乎都走光...但他說完之後,全場由衷地致敬,響起了掌聲!
-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學不會,再多的自由都只是 放縱
- 面對瞧不起你的人,不要生氣,要爭氣... 對那些人最好的報復,就是讓他們「跌破眼鏡」!
- 為妻子插管灌食,就像是恩將仇報…從醫師眼中,看日本人追求「老衰死」的善終智慧
- 【有實力,也可以很美麗!】于美人 浴火重生,從「衣櫃只剩三件衣服」開始...
本文摘自《叛逆有理、獨立無罪》
作者: 陳志恆 / 出版社:圓神文化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責任編輯 / Planet)
(首圖來源:shutterstock)

 發表
發表


 我的網誌
我的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