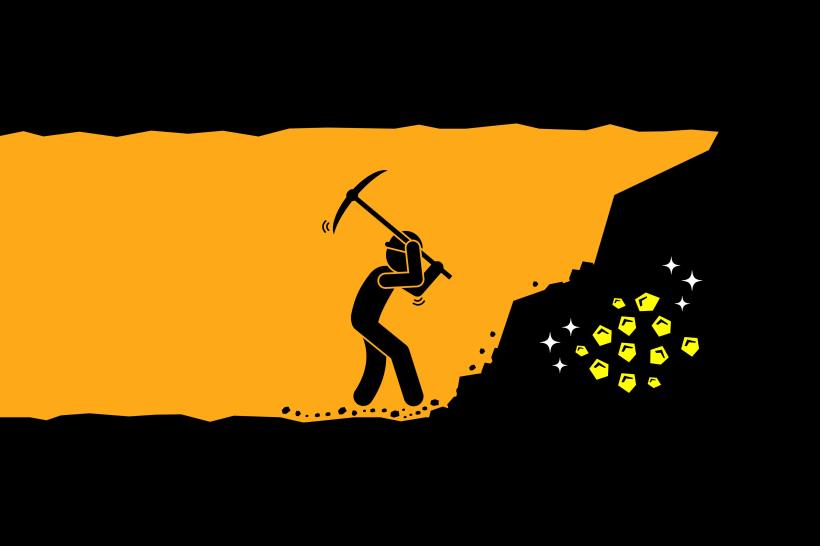
(圖/shutterstock)
在歐洲,墳地和教堂是一對孿生兒。
身邊有位女友,若是遇到墳地,
便會花個半小時,和它們靜待一會。
起初,她被各式墓碑吸引,
有的簡約,有的繁複,有的寥寥數字。
但無論逝者何人,都逃不開這兩段話,
你是誰,生於哪年死於哪日。
女友說,她還記得那個9歲孩子。
1998-2007,小小一塊碑,
周圍荒煙蔓草,寂寂無聲。
也許失足溺水,也許天生體弱,
也許只是運氣不好,但他離開了,沒有了。
唯有墳前的小雛菊,
訴說著,親人一直在惦記他。
生老病死,怨憎嗔痴。
甚至再也分辨不出,誰曾經為錢所困,
誰曾經偷過東西,誰曾經為愛癲狂。
在終點是死亡的這場遊戲中,
短暫的執著顯得毫無疑義。
反觀我從小所受的教育。
似乎,大人們一直避談死亡。
彷彿不問,不答,不提及,一切便不存在。
於是很多歉意愛意來不及表達,
於是太多時間浪費在糾結冷戰;
於是如何“好好說再見”這門課——
並非所有人,都提筆有資格,答卷皆及格。
十年前,第一次目睹親人離世。
太公是凌晨走的。
我看著花瓣撒上,花圈燒掉,
人就變成了小盒子。
那時天沒亮,屋裡很暗。
我閉上眼,以為他還在。
等我放假回家,帶我各處溜達。
他說哪裡新開了蛋捲店,要買回來嘗一嘗。
葬禮結束,
沒法和任何人交流,也沒能學會釋然。
我把太公的老年證,藏在身邊,放在枕下。
幾乎每個晚上都在想,
他怎麼還不託夢給我,
他在那邊過得好不好。
以前怕鬼,不敢多看恐怖片。
當時卻希望,走夜路能碰上,至少見一面。
因為放不下,因為太牽掛,
太公沒來看過我。哪怕是夢裡。
直到現在,
我依然避談“死亡”這類字眼。
甚至不敢去想,這個終將到來的事實:
所有身邊人,熟悉的,
在乎的,喜歡的,都在且行且遠。
在時間的無垠曠野裡,我該如何面對?
又該怎樣正視這些離去?
就像一滴水, 又消失在水裡。
變成漣漪,變成湖海,變成寒雪霜降。
它洇了開來,散了開去,白茫茫真乾淨。
關於“告別”,收到很多私信。
或寡言,或碎語。
每次最怕看到,那些懷著歉意的心事。
離去的人,遺失的物,錯過的再見…
“未完成的事件”就像魔咒,
會把人拉進情景黑洞。
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瑟縮的無助。
想起這些年,我跟媽媽常會爭吵。
她並非溫情的慈母,我也不是懂事的乖女。
倆人針尖對麥芒,處著處著就厭。
但何嘗不知呢,
微信列表中我是她的永遠置頂;
半夜醒來,只要她睡旁邊,
我翻個身繼續睡,便能一夜安眠。
我們相依著,相像著。
眼中看不慣,嘴上不服氣,心裡卻不捨彼此。
-“畢業後你打算去哪?留在杭州嗎?”
-“媽媽在哪,我在哪。我要照顧好她。”
雖無野心,也無大志。
但我不想以後賺錢了穩定了,
再去聊表孝意。
只想趁爸媽健在,
陪他們買菜做飯,茶餘飯後敘家常;
只想帶他們開車兜風,
珍惜雞毛蒜皮的短暫相處。
時間本就正反兩面。
子女的成長,必定伴隨著雙親的衰老。
他們傾注所有的愛,我不能回饋一二。
那該多遺憾。
遇到花海就漫步,
欣賞完再趕路。
仍記得,《我們這一天》裡的那段對話。
老去的威廉,找到被遺棄的兒子,
想好好彌補舊時光。
他卻發現,自己時日無多。
有人問他,“快要死了的感受是什麼?”
威廉說,“就像美好瞬間都化作了碎片四下翻飛,
我試圖抓住它們,它們卻從指間流走得更快。”
回頭看,現代人什麼都攥得太緊。
腦袋被塞得很滿——應試,績效,房貸;
身體更力不從心——熬夜,加班,焦慮不堪。
他們忙著升職,忙著賺錢,
忙著結婚,忙著養家,快到無暇自顧。
卻忘了,死生之外無大事。
太多汲汲以求之物,只是工具,並非道本身。
比起怕失去,怕失敗,怕錯過,怕不能重來——
倒不如,腳磨破就換雙鞋子,別再無謂硬撐;
遇到花海就漫步,欣賞完再趕路。
時間是盜賊,它予你生活,又一點點偷走;
時間更是良伴,它毫無保留,任你賞玩或寵溺。
願君多珍惜,莫說來不及。
盡情去愛,盡情去眷念,
盡情去完成想做的事。
終有一天,
摯愛卻分離的人會相見。
作者簡介:小燈泡兒,少女臉漢子心20+萌妹。
享受行攝在別處,沉迷吃喝難自拔。
微信公眾號:大櫻桃與小燈泡(iamcherry2016),
願與你分享有意思有意義的暖萌生活。
本文由 大櫻桃與小燈泡 授權 ,原文 於此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責任編輯/Kaedy)

 發表
發表


 我的網誌
我的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