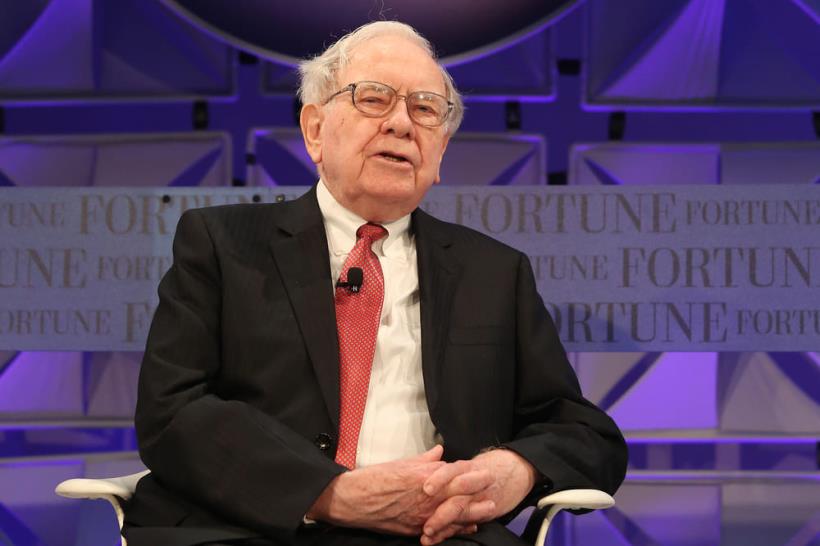
(圖/shutterstock)
上週週末,
筆者跟一票老美去柏克萊吃北京烤鴨,
在那觥籌交錯,擺滿珍饈的 10 人座原木桌上,
筆者的老婆發揮人來瘋的精神,
把場面炒得好熱,天南地北的議題都拿進來討論。
在場坐著一個當地小學老師,
負責學小學一年級的教育。
『他們現在在學校學什麼東西啊?』人來瘋問了,
想說答案不外乎是語言或是數學那類的東西。
繼續看下去...
(贊助商連結...)
取代語言、數學等學科
美國的孩子注重的是溝通與社交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老師不假思索的回答了:『溝通與社交啊』
『溝通與社交是那個階段最重要的事情了』
另一個老美接著說。
『那時候跟老師建立起來的情感 (bond) ,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腦中彷彿被一記悶棍打了一下,
我咀嚼著他們的討論,
這個回答有更深的文化意涵在。
兩位天才因為社會化的差別
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前幾年讀過一本加拿大人寫的書『異數』,
書中提到了兩位絕頂聰明的天才,
一位因為從小環境不好,
沒有人教他如何跟人進對應退,
儘管天資破表,卻在現實社會屢屢遭受挫折,
從沒有從社會那裡取得發展自我的資源,
最後隱居鄉間,過著孤芳自賞的生活。
另一位天才是中產階級出身,
儘管屢屢違法犯紀,
但是卻能夠利用絕佳的人際技巧左右逢源,
受到社會的原諒,認可與讚賞,平步青雲。
我想,這位老師的回答跟我讀到的這段有點關係。
我們小時候看醫生,
大多是父母代為發言,
跟醫生討論病情與診治的方法等等,
異數這本書
列出來的北美中產階級的教育方法卻不是這樣。
開車前往診所的時候,
北美中產階級父親或母親會先給孩子作心理建設,
醫生等等應該會問些什麼問題,
比如說哪裡不舒服,感覺怎樣等等的,
同時也教導小孩子可以怎麼回答,
等到了診所以後,
大人們會讓小孩子自己跟醫生對話與討論,
醫生主要的談話對象也會是小孩,然後才是父母。
北美的中產階級是這樣
無時不刻的教育孩子如何跟社會相處,
如何跟大人對話,如何適切的表達自我的需求與想法,
難怪你在火車上,飛機上,
酒吧裡會看到他們一派輕鬆的跟陌生人搭訕聊天,
到了一個全是陌生人的場合,
也很快的能夠找到自己需要的資源,
我們也會覺得他們從小就很獨立,有擔當。
反觀台灣教育,
從小到大大部分的決定都是父母捉刀,
面對世界,父母都會站在小孩的前方主導,
由於疏於練習,
跟陌生環境溝通能力從來沒有建立過,
出了社會一切重新訓練。
行銷跟溝通有很大的關係,
你所不知道的溝通與社交
在硬體與代工的時代,
我們只要向世界證明我們的良率比別人高,
同一個規格,我們的成本可以更低,
或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快,
但是到了品牌,軟體,與服務的時代,
考驗的是把『問題』轉化為『產品』的能力,
考驗的是讓『概念』藉由各種管道,
快處『傳遞』的能力,
考驗的是把『一盤散沙』組合成『一隻精兵』的能力,
以上三種能力,
分別是產品管理,行銷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
全都是由溝通與社交組成。
不管產品管理如何發展,它的核心價值
不外乎是把人類的需求轉化成產品的規格設計,
並實作出來,你當然可以照著教科書上面的方式
作問卷跟用一大堆 MBA 量化的方法分析,
但是在銅板的另一邊,
質化的方法同樣也是無可或缺,
而質化方法的基礎,
基本上就只是跟對象好好的坐下來
討論他們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行銷管理整個聽起來就跟溝通有很大的關係,
筆者認為,
其中一個最難的部分在於精準的表達出你想傳達的訊息,
你可以花大錢,用各種管道傳達出很混亂的產品訊息,
對公司整體幫助不大,或是精準的把所有的資源
都投資在一致與有效的溝通訊息上面,然後 Just do it。
最後,一個人是沒有辦法成事的,
你需要有你的團隊,於是問題來了,
人家為什麼要聽你指揮?
絕對不是因為你是創辦人或是官做得比較大,
你需要運用絕佳的溝通技巧去傳達你所擘畫的願景,
你必須要使出渾身的人際技巧
讓大家跟隨你的步伐往前衝刺,
沒有溝通與社交這兩項能力,
根本不會有團隊可言。
然後,跨國,跨文化地作。現實是,台灣市場很小,
很多產業如果只靠我們的內需市場,
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就算全台灣的 PC 全都用宏碁的,
也沒有辦法養得起宏碁這間公司。
宏碁 2013 Q3 PC 出貨量是 666 萬台,
夠整個台灣 1/4 的人口換全新的電腦,
但是宏碁 2013 整年是在虧錢的狀態,
換句話說,不賣國外市場,
就算全台灣每個人買一台,宏碁的 PC ,
當年度宏碁都沒有辦法轉虧為盈),
因此,我們如果要發展一個國際級的品牌或是服務,
溝通與社交的對象
也絕對不能僅僅是我們早就爛熟的台灣同胞,
要在別人的市場成功,我們必須要能夠精通
不同文化國籍的市場溝通與社交才行。
矽谷工程師坦言:
外地人很難將人際關係延伸到主流社會
這其實非常困難。
筆者到矽谷工作的這段時間,
發現如果不是從小就在當地生長的 ABC ,
長大後,尤其是大學後才到這邊來的菁英們
很難打進這裡的主流社會,
假日會跟一幫同是台灣來的朋友混在一起,
如果當地台灣人少些,
交遊的對象很可能就會加入中國人與香港人,
人際關係鮮少延伸到市場的主流社會。
這些旅居矽谷的人各個爛熟英文,
托福/GRE 考得比美國人都還要高,
所以這不會只是個語言問題這麼簡單。
連海外旅居人的人際關係都是如此了,
更何況身在台灣的品牌與服務,
想要打進海外市場,
想要對海外的消費者溝通出自己的價值了。
想融入異文化,
你只能完全的表現自己
看到這裡,
你可以很草率的下個比檸檬還酸的結論:
『這一定是因為文化歧視』,
但是就我的觀察,這絕對不是原因。
正因為北美這邊是一個強調溝通與社交的社會,
只要能用他們習慣的方式跟他們溝通,
很直白有自信地表達自己,
不要讓人家猜測,
你很容易深入地跟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會先跟你單獨出來在酒吧喝酒聊天,
慢慢開始邀請你到他們的家中,
最後把你納入他們生活圈的一個部分,
你會慢慢了解他們的思考邏輯,生活習慣,
如果你是員工,
你會知道怎麼在他們的文化下成功,
如果你是創業家/公司,
你會學到他們設計/衡量產品服務的想法。
台灣人才的硬功夫真的了得,
基本上只要開好規格,
哪種硬體軟體都可以做得出來。
很可惜的是台灣內需
不足以養活國際規模的大型公司,
因此我們必須要向外走。
向外走需要跨文化市場的溝通與社交,
台灣本土家庭與學校的教育
卻從來很少強調這兩個能力的重要性,
更何況是跨文化的運作了。
所以,下次帶小孩去看醫生的時候,
教他如何自己跟醫生說吧,
讓他早一點開始練習跟世界的社交與溝通。
本文由 台灣工程師的矽谷故事 授權轉載,原文 於此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責任編輯 : CMoney編輯/ ㄆㄆ

 發表
發表


 我的網誌
我的網誌


